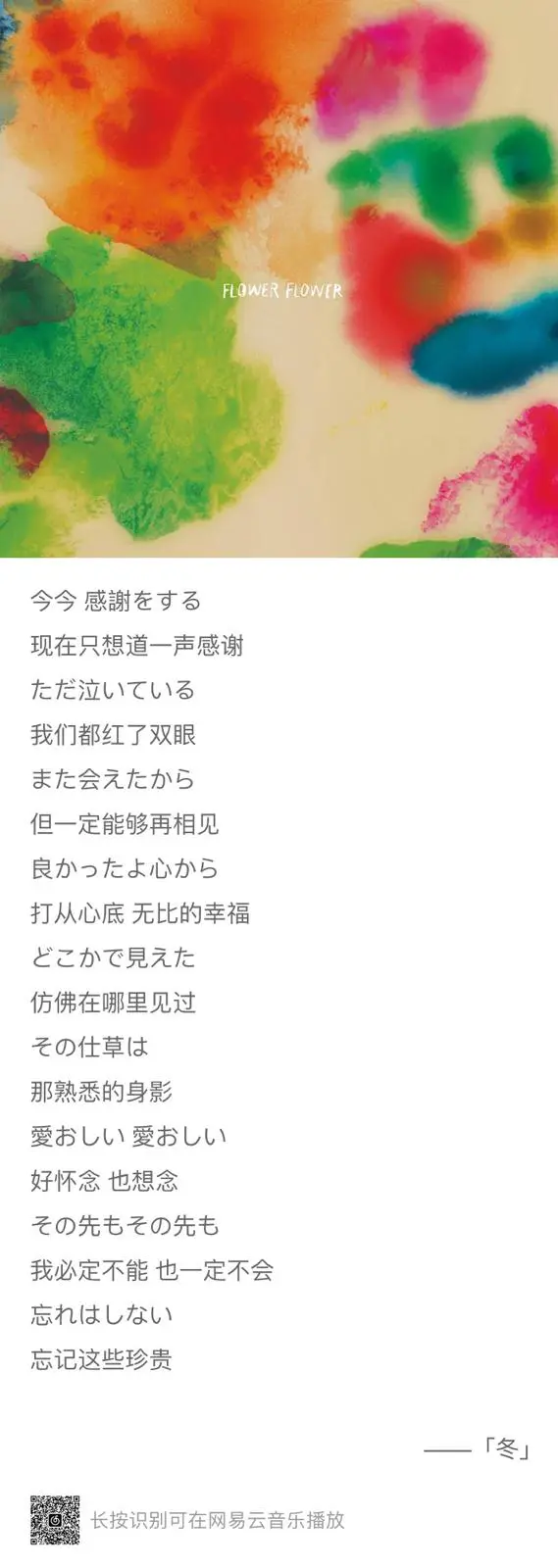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心疼十几年前的自己。
半夜在梦里被喊起来,阿姨告诉我:“你爸爸想见你。快把衣服穿上我们走。”被牵着走到医院,住院部门口站着好多人。一进房间,妈妈哭着跟我说:“钱琨,你爸没了。”大人让我再亲亲爸爸,我把脸贴上去,爸爸的脸是冰凉的。脸挪开时,不知道是我的幻觉还是什么,我看到爸爸睁开了一只眼睛。爸爸没有骗我,他真的还想再看看我。我听见妈妈一直在哭,另一个大妈,是我妈妈的同事,过来宣布死亡时间。我显然还没睡醒,呆呆地望着桌子上的玻璃板,不知道该作何表情。我觉得我应该哭呀,但是哭不出来。
后来二姨来了,领着我先回家休息了,路上碰到了小舅,我看到他的眼睛红红的。我想起妈妈说过,她的兄弟姐妹中,爸爸最喜欢小舅,他俩最谈得来。回家就听见爷爷奶奶的屋子里传来哭声,爷爷喊着:“琨琨该怎么办呢?”奶奶因为之前中过风说不清话,只是一直呜呜地哭。后来我就休息了,我听见二姨在我边上的呼噜声,觉得他们连夜赶过来,也确实是很累了。但我好清醒,好像一晚上没睡着。早上还是按点起床,从冰箱里拿出昨天买好的蛋糕,泡了一碗牛奶,吃好早餐上学去。
走在路上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我跟别的小孩不一样了,但我也说不出是哪里不一样。低着头看着脚一步步向前走,眼泪一下就出来糊了眼睛。在学校上完一节课,班主任在门口喊我,我起身时还没有什么,班主任揽着我的走在走廊里的时候,我突然扁着嘴哭了。老师拉着我到她的办公室,问我吃了早饭没有,我说吃了,她说有什么事情要请假就讲,我说好。还有其他什么不记得了,印象深刻的只有一句话:“不要在妈妈面前哭,妈妈也很不容易。”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记得这一句了,一记就是十几年。
中午从学校返回家吃饭,路上会经过厂里的布告栏,我看见爸爸的讣告,满满当当写了好几页纸。以前也见过讣告,但是头一次见到内容这么详实的。好多人围着看,我听见有人感叹,说还这么年轻。这么长的讣告我也只记住了开头一句生卒年月,和“享年四十三岁”。后来我问姑姑,怎么能是享年呢,爸爸还那么年轻,他享受到啥了呀。这之后我再看到故去的人的介绍,总是习惯性算一算年龄,超过43岁的人,我便觉得他活得蛮久了。
吃过午饭,我去给爸爸烧纸,姑姑这才得空给我换了外套,把红色的羽绒服换成浅蓝色的。我们走在路上说了什么吗,记不得了,我记得好像烧了7天纸,不知道准不准确。有天烧完纸,姑姑问我要不要看看爸爸,我说好,她便让旁边的工作人员打开冷柜的盖子。我看到爸爸安静地躺在里面,脸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工作人员让我别害怕,姑姑冷冷地回了一句,自己的爸爸怎么会害怕。
爸爸离世后,妈妈和爷爷都瘦了好多,憔悴了很多,我还想,我怎么没有瘦呀,感觉有些对不起爸爸。但其实我每天都在流眼泪,眼睛像是泡在盐水里一样。爸爸去世后的一周多都在下雨,好像老天也在掉眼泪。
出殡那天起得很早,大人们让我摔了之前烧纸的盆子,然后让我抱着爸爸的照片走在前面。追悼会来了很多人,先是有人念了爸爸的生平(记不得是谁念的了),我和妈妈姑姑站在旁边,旁边有认识的阿姨搀着我,好像怕我昏倒过去。可我听着爸爸的生平,越听越自豪,人也越发清醒,虽然不记得内容,但还是为有这样的爸爸感到骄傲。之后就是大家走过爸爸的遗体,再和家人们握手。我的手很冰凉,很多看着像是领导的人和我握手,也就是轻轻碰一下,走了个过场。后来妈妈走过爸爸的遗体,哭着说,钱钧呀,我们说好的,下辈子你做女,我做男,我们还要做夫妻。
追悼会结束,爸爸要被推去火化了,我看到妈妈扒着推车的边,手臂环着爸爸的上身。好多人拉着她怕出事,妈妈挣开说,我没有其他意思,我只想再看一眼,说着用双手捧着爸爸的脸摸了摸。这之前爸爸是化了妆的,脸上打了腮红,好像整个人有了气息。再后来就是火化,我听见别人说爸爸被推进炉子了,我抬头看,烟囱上冒了好多黑烟,我想,人就这样不见了呀。我还听见有人说人的骨头不能完全烧完,没法烧成灰的要人工压碎才好放进骨灰盒。好像是爸爸的骨头在被压碎,我听见了,嘎吱嘎吱的,我想看,但是舅舅挡在我前面,不让我看,可能是怕我看了伤心。
骨灰盒上的照片是爸爸生病前拍的一寸照,黑黑的偏分头发,精神的双眼,红红的嘴唇。火化后没有马上下葬,骨灰盒在墓地附近的水泥格子里放一段时间(具体这个地方叫什么不太清楚)。这期间是烧了很多回纸吧,爸爸三月份过世,直到夏天才入土为安。下葬那天我还是走在前面,这次没有抱着照片,我抱着的是爸爸的骨灰盒,沉甸甸的。一瞬间很恍惚,一个人最后就化成这么些了啊。在这之前的两年,表妹刚出生,小婴儿我也是抱过的。怎么一个人出生到故去,重量也会这么相近呢?果真人在世上走一遭,是什么都带不走的。墓碑立好了,落款的家属名写着我的名字,这应该是从此以后我和爸爸距离最近的地方。
写下这些是今年6月中旬,现在再整理发出,应该算是年底的拾遗补阙。之所以记录下这么多回忆,是因为那段时间好朋友的爸爸突然离世,她在向我倾诉的时候,也勾起了很多往事。我以为我会忘,其实早已根植于心。爸爸走后我很少梦到他,即便梦到,梦里的他也缄默不语,沉默地做自己的事。但他依旧拥有病前那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脸色红润,是一个健康的中年男子,也是我们一家人曾经希望他能恢复好的样子。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当时在读双雪涛的小说。双雪涛不止一次写到,“我”在送别父亲时,在灵车开动前,狠狠地将那个盛满纸钱灰烬的盆子摔得粉碎,然后大喊了一声“一路走好”。这一幕文字很平淡,但对我来说太过生动,瞬间将我拉回十几年前那个还未完全入春的寒冷清晨。我也是这样摔碎了盆子,抱着爸爸的相片,一路向前走。
已经很久没有回家给爸爸烧纸钱了,开始的几年是在春节除夕夜,和妈妈一起去烧纸。每次下楼,路口的位置已经有大大小小黑色的“圈”,那是其他家烧过的纸钱。每次烧成灰烬的纸钱飘起来的时候,妈妈会说“收到了,收到了”。在这里没有人会提那些科学道理,只是希望还能和故去的亲人有些微小的连结。
又到年底,今天是爸爸的生日,而明年就是他的本命年,但真正属于他的本命年,他也只过了三次。想象不出花甲之年的爸爸是什么模样,现在也不去想了。他已经停在最好的年华,我现在应该更加珍惜身边的亲人们才是。还有一点想象不到,如果一个人已经知道自己的时日所剩无几,他会做什么呢?对我来说,爸爸没有做其他的,他在2006年的1月,和我一起庆祝了最后一个我们全家都在一起的我的生日。足矣,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