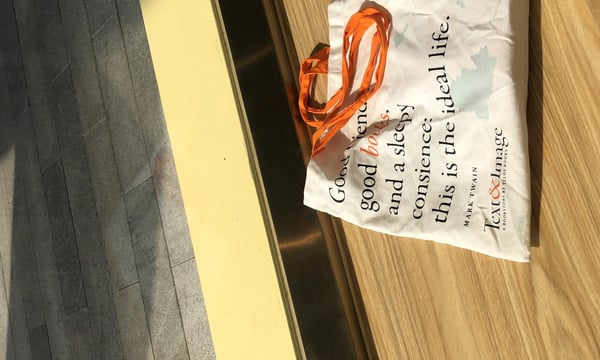写在前面:和Lucky学姐的第三期的夏日协同写作,共读书籍是 《忧郁的热带》, 本篇内容讨论了两个主题,书籍的内容和作者本身。最后成文的结构出乎意料, 不过这或许正是有趣的地方。
《忧郁的热带》是一部人类学田野笔记,也是一位人类学家的思想录。它不负责为你解答任何问题,它所能提供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疑惑。 ——Lucky

关于远方|旅行和探险的意义
【Lucky:真实从未终结】
“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作为一个注定离不开旅行和探险的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的著名开篇无疑展现了一种叛逆的姿态,他似乎在充满悲情地向世人发出警告,“探险已成为一种生意”,“真实的旅行故事已不可能了”。
或者,亚历山大·冯·洪堡式的好奇心如今已然是稀缺之物,又或者,它从未俯拾皆是。
除了少数人拥有对知识与未知纯粹的好奇心之外,大部分的旅行与探险活动都难免包含着某些功利性目的。地理大发现时期那些动人心魄的海上航行,如果说完全归因于人类为了丰富自己对于地球的了解,那么后面几百年的历史都会改写。事实上,追求资源和财富,才是耗资不菲的船队得以出发的主要动力。
抛开物质利益不说,若是缺少分享的途径,好奇程度也很可能随之减弱。偶尔刷一刷21世纪的社交网络,精致的旅行照片就会地跳到你眼前,小红书的忠实用户对于此类社交动态一定有更深刻的理解。这是因为,至少有一部分人并不是被好奇心驱使才去旅行,而是通过旅行(或探险)向其他人展示自己具有这样的好奇心。
在此有必要就展示的中立性稍加阐明:不管为了生理还是心理上的好处,展示自我都是种十分平常的欲望,它发生在几乎所有的生物身上,失去了这种欲望,世界将变得无比乏味,甚至根本无法持续。
不过,斯特劳斯显然也没说错,探险与旅行已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现代消费主义的一部分,用以满足广大展示者的需求。不断涌现的社交媒体及其用户的活跃展示,反复刺激着观众的神经,于是更多人渴望参与到这一展示的行列中去。展示者与未来的展示者就这样互相激励着,使得该类生意愈加红火。
以前的问题是,我们总是难以避免对远方产生理想化的预期,使得实际体验往往伴随着一种祛魅后的失落感;现在的问题是,无穷的信息途经各处涌来,关于远方的想象空间变得逐渐稀薄,曾经的神秘感几乎荡然无存。
我们当然可以说,丰富的信息赋予我们客观与理性的能力,可是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同时失去了许多心灵上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个时代,更应该担忧的是,尽管一部分有展示需求的人变得更加活跃了,但另一部分人可能由于过早过易地形成了关于远方以及关于旅行和探险本身的认知与判断,反而失去了对它们的兴趣。这样的消极情绪当然完全可以理解,可我仍然想表达的是,实际上,当我们在现实世界里向远方靠近时,其实也就是在靠近真实。
或许到处架起的拍摄设备令人心烦,我们不得不为找一个清静之地而大费周章;或许原本的面貌早已被破坏,我们无法看到古代旅行者所能看到的东西。但是,一切依然是鲜活而真实的。这种真实虽然看起来很新,同时却也是一层又一层时间的叠加,是一代又一代人类的活动的叠加,更是所有旅行者的观察与参与的叠加。
正如斯特劳斯谈及诸如纽约、芝加哥、圣保罗这些“新世界的大城市”时所说的,“缺少过去的痕迹,正是这些城市的意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斯特劳斯大概也并不像自己哀叹的那样不再对“真实的旅行故事”抱有信念,毕竟如此多的抱怨也没有使他停止过旅程。值得再三重复的是,一切发生的皆为真实,哪怕是为了展示而刻意雕塑出的故事也是一种真实,其中的真实性不在于故事本身,而在于”刻意雕塑“故事这一行为本身。
所以斯特劳斯读者们,无需因为他开头的警告而觉得过分沮丧,享受这门生意带给我们的便利,追寻每一处可及的真实。我们的一切所思所说所做,都在勾勒着远方的形象,也丰富着我们自己。
【Chuwen:重新想象远方】
认同Lucky对《忧郁的热带》里忧郁开篇的另一种解读。的确,远方的真实无论是哪一种真实,都依然可以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从句子中抽离就可以看到,虽然斯特劳斯悲观地预测“远方不值得探索了”,但是同时作为人类学家的自己依然“绝望地”多次往返。
信息轰炸的时代是一个矛盾的时代,人们的确更容易获得有关的信息,但这些信息有时也限制着我们对于远方的想象。繁华商场和好山好水有无数的足迹和无数的向往;而书中所写的偏远地区却无人知晓,“落后”是大多数人对那里全部的想象。
人类学的书籍无疑是例外,正如斯特劳斯对四个印第安部落进行了详实的描写,包括社会结构、生活情况和家庭构成。他们有很多共性,比如那儿的人们都不上学,基本不穿衣服(除了护阳具的饰物); 但也有自己的特别之处,譬如卡都卫欧族会在脸上和身上的画花纹;波洛洛族有半族制度划分的方式以及每当族里有人去世,剩下的人要进行一次集体狩猎仪式。
以一个“现代社会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内容或许可以轻而易举地总结“不文明/落后”。毕竟,身体本来是最珍贵的,不但不穿衣服还画画;有人逝去本来是值得哀伤的,不但不守灵还集体打猎。按照现代的逻辑的确言之有理,但合理的评判就是恰当的吗?未必。继续读下去就会看到其他的文化里会有更多的纬度或者另一套逻辑。
有的文化与我们的相距甚远但自成一体,如波洛洛族的文化里,人类不完全属于大自然。一位族人去世意味着自然夺走了一部分人类的资源,应该补偿一只大型动物给人类社会。所以狩猎不是因为冷漠,而是在讨债罢了。有的地方食物紧缺但是人本身并不匮乏,如南比克拉瓦族的物质条件的十分艰难,但作者感受到的并不是穷苦之下的戾气。反之,他深切地感受到族里夫妻之间的和睦,他感慨到“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庞大的善意,一种深沉的无忧无虑的态度,一种天真的、感人的、动物性的满足”。
现在回看,给远方直接贴上“落后”的标签其实某种程度在限制着我们的想象。斯特劳斯的“甜菜理论”显示了这种俯瞰式总结的局限性:
目前的肥沃土壤是可以是精心栽培出样式繁多的植物花卉。可是人类选择只种一种植物——大众文明,好像是甜菜那样大批大批的种植,从那以后,人每天享受的只有那么一样东西。
在目之所及都“吃甜菜”的环境之下,容易有全世界应该都“吃甜菜”的惯性思维,好像我们只能用同一个标尺在量度——文明/甜菜。文明国家的就是好的,距离越远就越落后。但是只用这一把标尺量度世界的方法其实是扁平且单一的,而且结论没有细节和来龙去脉。
这种“都应该”的观念看起来是因为了解,实际上是“现代人”思想中的想当然,是一种思维的谬误——过度简化(Oversimplification)。这种思维模式并非故意为之,借用 《事实/Factness》 里的比喻,对于住在20楼的人来说,住在10楼的人与住在2楼的人看起来一样高,因为他们都可以用“比我矮”来概括。所以不是说楼层高的人故意对楼层更低的人缺乏想象的,这种扁平化的想象或许是一种本能。
同样,身处于已经历过长时间发展的社会的我们,或许有些时候也并非故意简化对其他社会的理解, 但是这种本能背后高傲自大的姿态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回顾我们在贴标签时,其实完全不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没吃上甜菜或者他们在吃什么,因为这样的问题都不重要,反正吃不上甜菜的他们就是落后的。这样的想象,出发点不是好奇心,而是比较;结论不是我们不一样,而是他们没我好。我们没有了解到更多元的世界,只是获得了一种廉价的优越感。
想必斯特劳斯并不是在批判文明,毕竟他的思想和眼界,甚至他能在三十年代去拜访这些部落的机会都是文明发展的功劳,他想提倡的或许是一种文化谦卑(Cultural Humility),对其他文化怀着好奇心和敬畏之感。在下一次有机会了解“现代意义”上“没那么文明”的地区时,先别一杆子打死,多问问问题,听听看,说不定会有更多收获。
真实的旅行故事即使不存在了,但真实的理解依然可以发生。
关于作者:人类都是多面体
【Chuwen:一杯赞美的甜酒】
斯特劳斯的哲学受训背景让他为这本书增添了很多跨学科维度,他根据自己遥远他乡观察到的景象进行的思考,恰好对应着我自己内心的很多困惑与矛盾,以至于我好像有一种超越时空被理解了的快感和释然。即使他吐槽了很多哲学的内容以及哲学不适合他的原因,但依然不可否认他“走错”的这段哲学之路功劳不小。
首先他更老了,这段哲学之路给了他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建立自我意识。
如此多关于这段岁月的困惑正是他进行了很多思考的证明,自己是谁,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困惑之中他对自我的认识悄然形成;自我意识的形成为书中坦诚的反思打下了基础,他对于世界的复杂性有包容的态度,并且愿意直白地表达出来。
比如,他对人类学家的反思,对于自己所属社会和异族社会的态度,承认自己对于自己的社会是更具有批判性的,更加负面的,而对于他观察的社会,却带着一种更加客观和包容的态度。正如迪迪埃·埃里蓬在 《回归故里》 的对自己成长经历反思,他通过教育这条路径跨越阶级的桎梏,但这条路径同时使他离自己熟悉的家越来越远。这种反思总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这是一种与原始的思维惯性“Mine is better”相悖的观点,是需要勇气的态度,毕竟“自我揭露”实际上是对部分自我形象的破坏。所以这种态度是有底气,是对自己诚实,是在自我意识完整之后才会生发出来的能量。
这弯路也为他后来的人类学研究增添了一块滤镜,让他在描写很多观察到的现象时充满了哲思,即使他批判哲学的思考方式,但是不能否认这样的思考方式让他为一些现象拓宽了解读的空间。
譬如他对比西印度洋的旧酒厂和波多黎各的现代酒厂的朗姆酒时,发现那些缺少保养的旧酒厂的酒更香醇,因为设备过于老旧而导致造酒的过程中有很多杂质。以此类比人类社会中关于文明的矛盾——
文明的迷人指出真实来自于沉淀其中的各种不纯之物(残酷,不义,贫穷等),但文明的发展却在于消灭这些不纯之物。
关于我们对这些不纯之物的态度,他提到“只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社会群体是不恰当的”,因为身处的环境不同,拥有的可选择范围不同,其实我们并没有评判其他社会群体的权利和视角;但同时,他也提到,如果将上述的反面做到极致,即”毫无差别的拥抱所有的社会和习俗,这种折衷主义(Eclecticism)也是也不太妥当“,因为这样一来,社会奋力抗争的不纯之物也会被通通赦免,社会便无发展可言了。
这两个极端某种程度上撑出了一片空间,也就是斯特劳斯抵达的结论——“其实没有完美的社会,每一个社会都无可避免的存在这杂质,没有一个社会是绝对好的,也没有一个社会的绝对坏的。所有社会都给其成员提供一些好处,但是毫无例外也附带了一定分量的恶。” 在现今凡事搞对立的时代,如此反乌托邦的、客观的声音无疑非常珍贵的。
不止斯特劳斯,在很多人的生命中,多学科的滤镜在岁月的见证下多是有价值的。欧文·亚隆在精神科轮转时旁听了大量哲学课程,最后开创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著名的环保建筑设计师内里·奥克斯曼,先接受了建筑师培训,后来接受了临床医学的教育,最后把医学知识应用到了建筑材料上。阿詹(詹青云)从经济转到政治再转到法律,现在从事商业方面的法律工作。这样的经历总会在一开始被误解为不纯粹,或是缺乏科班训练。但恰好是这种不纯粹的过去可以和当下的学科相互碰撞,产生了更有趣的见解。
正如那一杯朗姆酒,不纯粹,却更有滋味。
【Lucky:一盏批评的苦茶】
毫无疑问,斯特劳斯是善于反思与批判的,这种特质既影响了他的学科经历,也影响了他从事学术研究时的态度,尤其体现在有意从一切经验中提取出最难以解答的问题,并揭示其复杂与矛盾之所在。如果我们能够同意,这些是成就一位具有启发性的人类学家的关键,也就不能不坦然地去正视斯特劳斯自身的复杂与矛盾。
通过对比南美与印度的资源和人口,斯特劳斯作出了这样的阐述:在南美,“不需要多少东西即可生活,人开始劫夺这块土地只不过是450年前的事,而且只在某些特殊地区进行掠夺”;而在印度,殖民者进来之前就已经面临资源短缺、人口过剩的问题。因此,“很难说资源丰富可以弥补空间不足的缺陷,也不能保证说一个富裕但人口过多的社会不会被其本身的人口密度所毒害”。
他在观点上的表达总是留有丰富的余地,让我们无法否认其中蕴含的正确性。然而,也正是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潜在地想要证明,征服与掠夺行为对本土居民造成的伤害是次要的,首要的是一个地区本身的人口密度所造成的伤害。
他甚至把三千年前种姓制度的诞生归因于为解决人口问题,以此来暗示,从始至终,这块“次大陆”都是一场因人口过密而无药可救的悲剧。先不说最初的种姓制度究竟是人群分工还是人群分隔的结果,斯特劳斯都忽视了英国在近代殖民统治中对于进一步固化种姓所起到的作用。
经历过19世纪的几次殖民地暴动之后,为了在南亚大陆更有效地进行殖民统治,英国人从已有的分类体系——职业与种姓中获得启示。如果说种姓等级曾经在印度还略显潦草和模糊,那么大英帝国的统治者便是义不容辞地担起了以更为“科学”的方式为印度民众分类的“重任”,将其正式纳入到印度政治之中,并以声称其历史地位与价值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人口问题与种姓制度自然对许多印度人民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但是英国外来者的介入原本也引入了另一种秩序的可能,可惜最终证实,这只是一种为了自身利益而选择的更具毁坏性的可能。斯特劳斯并未提及这些事实,即使我们可以将这解释为他对印度的历史不够熟悉,可是他对印度底层人民的描述也还是很难不让人觉得如鲠在喉。
面对那些饱受饥饿折磨又喜欢耍无赖的穷人,斯特劳斯既表现出深刻的同情,也绝不愿掩饰随之而来的厌烦。他犀利地指出,“如果你任由同情胜过谨慎,而给那些无望的人一些施舍的希望,那个人很容易一下子就变成一群号叫的暴民”,并且不断强调印度底层人民是多么习惯于遵守自己的阶级地位,以及从这一切不平等的关系中赢得好处。他的叙述中尽管包含着的自嘲与讽刺,但这同时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他们不愿成为与你平等……他们并不要求任何生活的权利;生存这件事实本身,他们并不认为值得施舍,只有他们向有权势者卑屈颂赞才值得得到施舍……我们不得不拒斥这些祈求者,我们拒斥他们,并非因为我们鄙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用崇拜败坏我们,他们想要我们变得更堂皇,更有力,因为他们疯狂地相信,只有把我们抬高百倍,他们的处境才能有些微改善。这一点相当能说明所谓亚细亚式的残酷的根源。
这样的解读,的确展现了一种“残酷的根源”,可更残酷的是,它仍然出自一个被崇拜者的视角。其中的绝望语调,巧妙地弱化了被崇拜者本身作为天然剥削者的角色,从而使得他内心的罪恶感得到一定程度的释然与抚慰。然而,这些印度人真地“不愿”平等、真地“相信”抬高他人的好处、真地存心要用“崇拜败坏”这些白人吗?还是说,他们只是“不得不”而已,他们只是别无选择而已。更不用说,有多少底层民众是被英国殖民者创造出来的,但是关于这一点,斯特劳斯依旧一无所知。
他一次又一次地忘记了英国人的存在,似乎这些不速之客们就像蚂蚁一样无足轻重,从未对这个国家与其人民产生过任何影响,甚至可以在印度历史中轻而易举地隐匿于无形。
与这种关于殖民统治的无知相对应的,是斯特劳斯对伊斯兰教的熟稔。他不仅谴责穆斯林在这片土地上进行的霸凌,更谴责其教义本身的自负与残酷。连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分裂问题,也以伊斯兰教的狭隘一概解释。不仅如此,它更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巨大阻碍,是横亘在基督教世界与佛教世界之间的壁垒。在斯特劳斯的想象中,如果伊斯兰教从未存在过,东西方早就能够和谐共处,基督教与佛教早就将这个世界变得博爱大同。令人惊讶的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斯特劳斯,仍旧能够保持着这样一种天真。
结语:辩证法
【Chuwen:关键词——局限】
上面的对话我愿称之八月最有意思的一段书写。
读到这里的读者或许不免有些困惑,我和Lucky一个夸另一个踩,这个作者到底是怎么样?刚开始我们也会担心这是否是自相矛盾的体现?这种担心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沉默的预设——一个作者对世界方方面面的认知都应该是恰到好且足够正义的。而我和Lucky的对话过程可以理解为推翻该假设的证明,即说明了人和社会一样,没有完美的,只有复杂的。
人在不同面向的确是会有局限性的,作者可以在对某些种族表现出极大的包容和理解的同时,对某个种族带有偏见和评判。再退一步,即使作者的观点在全书保持一致,读者也可以赞同某一部分不赞同另外一部分。有局限是正常的,这才是人类真实的面貌,也是发展的动力和契机。需要避免的是回避局限,以沾沾自喜的态度指指点点。
【Lucky:关键词——对视】
Chuwen与我其实也代表着人类思考的不同面向,但是我们之间的交流从未产生过不愉快,这是因为,我们既从各自的观察角度分别出发,也同时从对方的阐述里寻求补充,两者并不冲突,且后者尤其重要。
理解世界不止是走出洞穴的过程,还一定要通过不断对视才能达到,可以是与书本的对视,可以是与风景的对视,也可以是与他人的对视。无论如何,对于一个紧闭双眼的人,洞穴内外是没有区别的。